欧洲站女装:恋老部落-消失的日本中年劳动者:任何人都有与社会脱节的风险
一个从美国经济的“谜团”中浮现的存在
首先,厘清一下“消失的劳动者”这个概念。
“消失的劳动者”,是专门研究劳动政策的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提出的概念。如前所述,尽管自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以来,美国失业率稳步下降,但并没有出现经济复苏和工资增长的迹象。这一大经济“谜团”引起了该研究所的关注,成为提出“消失的劳动者”概念的契机。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在其报告《消失的劳动者》中对上述经济谜团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现如今的劳动市场中,失业率这一指标无法有效涵盖就业机会较弱的群体,造成失业人数被低估。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存在诸多未被计算在失业人数中的‘消失的劳动者’,他们并不处于失业状态,而是干脆放弃了工作(即不愿寻求就业机会)。”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1日,从美国新英格兰到得克萨斯州的数千名码头工人进行了罢工。
换句话说,失业统计数据并不包括不再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因此尽管这些人没有工作,但不会在失业者统计数据中显示出来。实际上,许多处于失业状态的人被忽视了。对此,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做出了以下解释:
“消失的劳动者”因其就业机会较少,往往不会积极地寻找工作。也就是说,那些具备足够就业机会的人实际上要么正在工作,要么正在寻找工作。失业者仅在积极寻找工作的情况下才会被统计为“失业者”。然而,由于“消失的劳动者”缺乏就业能力,也没有积极开展求职活动,并不会反映在失业率数据之中。正因如此,才有必要以可见的方式对这些“消失的劳动者”进行数据化的统计。
有鉴于此,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对本国“消失的劳动者”的规模和趋势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统计,从中间阶层的角度分析美国经济,并计算了相应的估计值。他们将这些估计值提供给国家机关等机构,提出必要的建议,使得数据能够服务于政策制定。具体的估算方法基于高度复杂的专业计算公式(具体可参见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www.epi.org——原注),但简而言之,相关统计结果主要通过跟踪“劳动参与率”的历史数据估算而来。
根据估算,首先可以发现,自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以来,“消失的劳动者”的数量急剧增加,最多时有近400万人。从年龄分布来看,绝大多数“消失的劳动者”是45岁以上的中年群体。如果将这些人数加入重新计算失业率,可以发现在2015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从原本的5.1%上升到了7.4%。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失业率这个数字应该是“实际未就业人数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因此,可以认为当时美国政府公开的5.1%的失业率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实际情况。更接近实际情况的数据应当是7.4%的失业人口占比。
日本版“消失的劳动者”
在日本,长时间闭门不出的“家里蹲”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可以认为,“消失的劳动者”很有可能也处于一个相当大的数量级。于是,日本放送协会特别节目组咨询了时任日本总务省统计研究研修所研究员西文彦,拜托其推算出“消失的劳动者”的大致数字。西文彦研究员是统计专家,曾在日本放送协会特别节目《老人漂泊社会》中分析过日本的国家统计数据,揭示了与父母同住的未婚者的数量及其经济状况,并提醒了这些家庭存在“亲子同倒”(即子女为了照顾高龄父母而与父母同住,导致生活质量大幅降低)的风险。

2019年2月12日,日本东京,工地上的中年劳动者。
西文彦研究员指出,各个国家的就业统计,都会在调查方式与问卷内容方面存在不同之处。如此一来,既然要尝试计算日本的“消失的劳动者”的人数,就应该将日本官方公布的《劳动力调查》中被纳入“其他”部分的人群算作“消失的劳动者”,从而与美国的计算方法保持一致。
《劳动力调查》根据日本《统计法》进行的“劳动力统计”的核心数据展开分析,旨在获得关于日本就业和失业状况的基础资料。每月,有关部门对抽取的四万户家庭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根据反馈的问答情况,推算出失业率等常见数据。
那么,所谓“其他”部分,又到底包括了哪些群体呢?调查问卷中,对在调查月份最后一周“完全没有工作的人”的分类包括:① 有工作,但是在休假;② 正在找工作(即对“失业者”的定义);③ 上学(主要是学生);④ 做家务(家庭主妇和家庭主夫);⑤ 其他。也就是说,“其他”这一选项代表着“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在找工作,并且没有上学或做家务”的一类人。
虽说倒也并非不存在非常有钱因此悠然自得、什么活都不干的特定人群,但其数量肯定不多,所以姑且可将被归入“其他”群体的人数大致廓定为日本的“消失的劳动者”的数量。
还有一点,被列入“其他”分组的群体,不用说当然涵盖了所有年龄段,但统计详情中的确还包括相当明确的各年龄段统计。美国的“消失的劳动者”集中于中年,所以我们也将在日本的数据限定在40至50岁,以期从中一窥真实情况。
既非“啃老族”,亦非“家里蹲”
在西文彦研究员的帮助下,我们探究了过去20年间日本“消失的劳动者”的数量变化情况。
结果显示,1997至2017这20年间,日本四五十岁的人口数量减少了16万,但其中“消失的劳动者”的数量,从73万增加到了103万,上涨了41%。
进一步比较2009年雷曼危机后和2017年的情况可以看出,同一代的“失业者”人数从11.3万减少到了7.2万,而“消失的劳动者”的数量则在100万左右波动,保持稳定。
因此,过去几年来的情况是,“消失的劳动者”的人数一直超过“失业者”。换句话说,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在中高年龄群体中,日本的“消失的劳动者”比例逐渐增加,并被甩在了经济复苏的进程之外。
很多人可能听过“啃老族”(对应的英文缩写为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原注)这个词。这一概念由英国社会学家提出,主要指代那些不在工作、不找工作,也不接受教育或做家务的人。尽管这样的解释似乎与“消失的劳动者”很相似,但在日语中,他们通常被称为“年轻无业者”,仅限于15至34岁之间的青年群体。他们从学校毕业或辍学后,不去工作、不找工作,整天在家无所事事,这在日本也被视为一个重大问题。而“啃老族”一词也在帮助他们寻求自立机制的过程中得到广泛使用。
日本各地都在推行帮助“啃老族”自立的支持政策,包括设立帮助年轻人就业的公共职业介绍所与自立帮扶中心等机构。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机制并没有将四五十岁的中年“消失的劳动者”纳入帮扶范围。正因如此,目前日本已经步入中年的“消失的劳动者”处于完全从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体系中脱离出来的状态。鉴于这一群体只能将高龄父母的养老金作为安全保障,社会保障方面的专家评价称,“未来会出现对社会产生重大反噬风险的危险状态”。
与“啃老族”相似却又不同的,是被日本社会长期视为问题存在的“家里蹲”现象。厚生劳动省将“家里蹲”定义为:“不去工作或不去上学,几乎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毫无交流,在家处于闭门不出状态六个月以上的人。”
“消失的劳动者”与“家里蹲”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存在重叠的部分。内阁府发布的“家里蹲”实态调查披露了最新的数字,2010年度“家里蹲”的人数达到了69.6万,而2015年度则是54.1万。
日本总务省对“家里蹲”的定义要比厚生劳动省宽泛得多:将“只因为兴趣外出”“会外出至附近的便利店”“几乎不从自己的房间中出来”等状态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人悉数纳入进来。但由于至今为止的调查都只针对39岁以下的人群,所以目前尚无法了解到40岁以上中年人群中“家里蹲”的数量。
然而,随着虐待、杀人案件频繁见诸媒体,日本社会中的“家里蹲”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被大肆报道,内阁府也开始了针对40至64岁“家里蹲”群体的调查。2019年3月发布的结果显示,日本全国40至64岁人群中“半年以上处于家里蹲状态”的,约有61.3万人。
有超过四成的“家里蹲”,是在40多到50多岁期间进入这种状态的,这一数据明确地体现出了中年陷入“家里蹲”状态的风险很高。而且,在陷入这一状态的人群中,虽然数据显示七成以上为男性,但由于女性可能会将“做家务与看护”视为劳动,认为自己并非“家里蹲”从而没有如实回答问题,也就是说,在女性群体中可能仍存在未被发现的“家里蹲”黑数。对此,将在后文详细说明。
总之,得到统计结果后,时任日本内阁府负责人表示,“今后需要出台针对非青年人群的支持政策,同时要让社会更广泛地意识到中年人群同样需要这方面的帮助”。
思考“消失的劳动者”的社会成本
简单来讲,“消失的劳动者”的影响在于,本应是劳动主力的四五十岁人群长期游离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极大的问题。
目前,日本正处于“慢性人手不足”状态,将老年人、女性、外国劳力引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当务之急。日本政府也提出了“一亿总活跃社会”政策(当时的安倍内阁提出的以提振经济、支持育儿、强化社保为中心的战略构想),必然要想方设法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但也正是这样的日本,还有100万以上处于劳动主力年龄段的国民偏偏游离于就业市场之外,“从劳动市场中消失”了。

一名男子走在东京地铁站里
在制造业等领域,企业因为人手不足而倒闭的案例比比皆是,并且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日本社会还存在着未被发现的劳动力。在这样紧迫的状态下,如何活用这些劳动力,找到让“消失的劳动者”回到劳动市场的对策,显然成为当务之急。
还有一点便是,现在这一批没有从事劳动的四五十岁人群,根本没有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足准备,更没有能力去支付养老保险费。也正因此,他们迈入老年后几乎都要依靠政府提供的生活救助才能生存。这一问题在未来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不容小觑。
同时,在很多家庭中,已经步入中年的孩子仍然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着“家里蹲”的生活,被逼入绝境的父母也不得不担心自己的身后事。日本各地司法书士会(日本各地司法书士的行业自治组织,司法书士主要负责商业注册、房产登记和司法诉讼档案准备等工作)接到的咨询中,想要在父母死后进行财产托管的案例也纷至沓来。即使在父母生前就将财产交给专业的法律人士管理,每个月转入定额的生活费,也不一定能够切实保障安定的生活,说到底,不属于这种保障能够涵盖的范围。
比从劳动力市场消失更糟的问题是,若蛰居状态长期持续,“家里蹲”群体就有可能从社会中“消失”。如果这样的话,支持这些人的生活起居将耗费巨额社会成本,另一方面,出现过多和区域社会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也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普遍不安。

“消失的劳动者”预备队的现实情况
在观察这些“消失的劳动者”时,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陷入穷途末路的困境,其实是因为每个人都曾遇见的平常琐事。
其中,看护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使在公司正常上班,但为了看护父母而离职的人,必须面对非常大的风险。干着兼职等非正式工作的人要换工作也很难,最后很容易因为看护父母的负担过重而完全脱离工作岗位,只能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
在此,还想重申一下之前的观点,看护父母与养育孩子不同,大部分情况下都会面临“越来越重”的负担。考虑到这一点,想必没有人可以表示这个问题事不关己从而高高挂起吧。
特别是女性,一旦步入中年,要是还做着非正式工作,换工作将会难上加难。即使成功跳槽,时薪也会慢慢降低,很多人都会面临经济上的风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看护的负担加大,很容易就会陷入穷困状态。
2018年4月,节目组与一位在非正式工作中反复辗转的女性不期而遇。这位女士为了看护父母不得不频繁辞职,但之后为了获取收入又会很辛苦地寻找新工作。但是,如果她下一次无法成功找到工作呢?如果看护的负担突然加大呢?如果必须放弃工作呢?她是不是就要被迫成为“消失的劳动者”中的一员呢?在这个意义上,这位女士当属“消失的劳动者”预备队中“货真价实”的一员。
为了直接与她对话,我们来到了距离横滨市日本旅客铁道株式会社保土谷站步行约15分钟的一个娴静住宅区的一角。这位女士就居住于此。位于高地的独栋住宅乍眼望去,竟让人有种富家生活的感觉,建筑风格优雅,与“消失的劳动者”的形象相去甚远。气派的房子让人不禁开始思考她的生活,想着这些,我们按响了门铃。很快门就打开了,仿佛她已等候多时,这位名为原真由美(化名,53岁)的女性热情地迎接了我们。
她说:“这里是我居住的合租屋。其中的一间房间归我住。因为还有其他的住客,拜托请保持安静哦。”
尽管外观是独栋,但实际上是由闲置房改造而成、专为女性租客设计的“合租屋”。厨房、淋浴间和厕所大家共用,每位租客有约四畳(七平方米)大小的私人空间。
由于与其他五位住客一起租用整栋房子,所以租金要比一般的单间公寓便宜。据说,在首都圈,利用这种空置房屋的合租屋的数量正逐渐增多。
由于在共用空间感到有些束手束脚,原女士领我们去了她的房间。一个看上去连四畳都不足的小房间,被单人床、小桌子和小衣柜塞得满满当当,大家都感到有些局促。但对于原真由美来说,这个位置相对靠近都心、租金又便宜的合租屋,似乎正是她需要的栖身之所。
原女士表示:“租金包括了水电等各种费用,总共是4.65万日元。如果再从市中心向外一点,应该会有更便宜的地方。但我毕竟是一个人生活,对我来说必须住在方便的地方才能生活下去。所以就选择了这里,位置便利又价格适中。”
原女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目前作为非正式的派遣员工,与横滨某区役所签了六个月的合同,负责进行个人番号注册等工作。这是一种被称为“非正式公务员”的职位。由于工作内容主要是进行数字输入等简单的操作,所以时薪不高。原女士自嘲地将自己的工作比作“流水线工人”。(个人番号[マイナンバー],又称为个人编号,是配发给日本所有国民和登记住民票的居民[包括外国人]的12位数字编号。从2016年1月开始,办理社会保障、税务和对抗自然灾害等相关手续时,都需要提供个人番号。)
“要说的话,这份工作的工资确实很低,会让我有一种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工作的感觉。工作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感觉自己就像流水线工人一样不停地重复劳动,虽然这个例子可能有点刺耳,但确实如此。因为是简单的工作,所以不付出相当努力,是赚不够生活费的。”
原女士向我们展示了她的薪资明细,上个月的税前收入是13.4852万日元。扣除了税金等杂费,实际到手10.8237万日元。这个数额还得扣除每天都得花的交通费,共6270日元,林林总总算下来,原女士的实际收入大约是10.2万日元,而这个月她一共工作了19天。
“这个月的收入可能还算是比较高的了。有些月份可能工作时间还不足19天。要是按少的来算,一个月的收入甚至可能不到10万日元。就年收入来说,可能还没有达到100万日元。”
日本宪法规定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即政府发放的生活救助金,是一个月13万日元(视居住地而有所不同)。我们问原女士,对此作何感想。
她回答道:“说起这个,也没有什么想法。我的收入甚至要比那些领生活救助的人还少。但是说实话,如果一个月能花10万日元,就能过得很宽裕,不觉得有什么很困难的地方。”
扣除房租后,原女士每个月还剩下大约6万日元,用这些来购买食物和支付其他生活开销。
“我觉得现在的收入也还可以吧。如果一个月都满勤,大概也就是这样子了。但如果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会更少。我确实是年纪大了,没法像年轻人那样干活麻利,所以已经‘躺平’,没那么拼命了。”
当然,原女士现在的收入也仅够维持基本生活,没有余钱购买衣服。两年前打折时买的半价外套就算是最新的衣服了,剩下的衣服看起来都比较旧,但她仍然敝帚自珍,表示已经养成了节约的习惯,衣服能穿得上就行,完全不会去想买更好的东西。
她补充道:“其实衣服不用每年都买,又不是不买就活不下去。总而言之,除了食物等必须购买的消耗品之外,我尽量不把钱花在其他方面。”
原女士对自己的餐费也格外节省。她会去便宜的蔬菜店进行大采购,每次只做一点,平时根本不会涉足价格比较昂贵的便利店和超市,在家大部分时间也只吃煮菜和意大利面。她会在狭小房间的桌子上仅有的空间放上餐盘,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独自进餐。孤独的背影,不由得让人感觉有些落寞。
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派遣合同就到期了
几天后,原女士的派遣合同到期。在横滨市区役所的一楼,设有个人番号登记受理窗口,在这里,总能看到她专注工作的场景。原真由美负责为来窗口咨询的居民提供服务、解释手续等。由于行政工作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她也曾努力学习个人番号制度和手续等相关知识,以便更顺利地为市民提供帮助。
当天傍晚五点,原女士结束了为期六个月的合同工作。窗口关闭后,有人告诉其他职员,原女士要离开这里了。
“诸位,今天是原女士最后一天来上班了。”
紧张的原真由美被催促着来到了聚集在一起的职员面前,慢慢地环视了一下大家。
“这是我第一次来公家单位,虽然工作时笨手笨脚,但大家给予了我很多指导,非常感谢大家。”
就在这一天,她再次失业。
原女士表示:“有些落寞,但也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份工作只会持续半年,现在也无计可施。结束了这份工作就去找下一个,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对于50多岁的原真由美来说,没有找到下一份新工作,情况确实相当严峻。
然而,对于不断更换短期工作的她来说,这已然是家常便饭,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原以为她会去找份长期工作,但看起来仍然要去打短工。
“虽然并非没有想过要改变现在的生活,但现在来看即使想改变也改变不了了吧。在潜意识里,或许就觉得自己不可能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无论心理上还是经济上,我都不认为自己能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我只是觉得不可能。”
原女士此前只从事过简单的办公工作,缺乏更丰富的经验,所以连自己想做什么工作都毫无头绪。但一旦承担巨大责任时,她又会感到负担沉重,正因如此,她才一直接受现状、得过且过。
而且,她从未对这一点产生过怀疑。
“我并不认为会找到什么好工作,有什么好待遇。都50多岁了,即使偶尔想想‘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能让我发光发热的工作吗?’,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大概是没有吧。人一年过半百,就不禁觉得(生活)开始走下坡了。”
在没有确定下一份工作的情况下,原女士过着看不到未来的生活。她全然不顾未来会怎样,就这样生活着,没有目标、没有梦想,也没有希望,只是日复一日地活着。虽然听着很让人绝望,但她时不时地还会绽放出快乐的表情,在交谈中也会展露笑容—或许她是一个内心坚强的人。
原女士还是袒露了心声:“到底要走向何方呢?我也不知道。我就像一个没有带地图的旅者,失去方向般地生活着吧。旅者心里总归有个目的地,但我心里没有。如果有目的地,我就会有地图,我看着地图,找到方向,指引着自己的生活。”
我们问她,这种没有方向、没有着落、不知道走向何方的人生,是否会令她感到不安?她的回答是坚定的——正因为不知道哪里是归宿,她才自由。
“我觉得没有目的地其实也没关系啦。因为可以过上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我每天过日子需要钱,我也只是为了钱去工作。”
原女士说自己并不想让生活变得更富足,她对自己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但或许就是通过不去追求更高的理想,她才让现在的自己悠然自得。
但其实她的内心还是会感到些许空虚:“这些年过着这样的生活,其实已经渐渐习惯了,觉得这就是常态。或许打心底里就是觉得自己过不上什么富足的生活吧。但有时候还是会觉得生活缺少了点活力,一片茫然。”
在泡沫经济中迷失
其实,原女士曾有过一段非常充实的工作经历。20多岁时,借着海外留学的经历,她进入外资证券公司工作。当时的她,作为派遣员工,时薪是2000日元。最多的时候,一个月的收入甚至能够达到40万日元。除工作外,日常生活也十分充实,每次长假,她都会远渡重洋去自己喜欢的地方海外旅行。
原女士给我们看了当时与公司同事拍的合影。在一家意大利餐厅里,她穿着时髦,与伙伴们围坐在桌旁,举起酒杯,比出“耶”的手势,脸上洋溢着笑容,那时的原女士可谓光彩照人。
但,彼时身穿西装、光鲜亮丽的职业女性生活,在她45岁时戏剧般地急转直下,原因非常简单,派遣工作的合同没有得到续签。当时雷曼危机席卷各个行业,许多公司纷纷进行了“派遣裁员”,处于弱势地位的派遣员工首当其冲被扫地出门。原女士所在的外资证券公司也不例外。
就业市场遭遇寒潮,新的职位几乎绝迹。原女士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一份月薪14万日元的饭店工作。她进入这家位于某地的企业,与一群20多岁的年轻员工成为同事。
原女士回忆:“薪水虽然下降了很多,但每天过得都很轻松,解放感压过了曾经的失落。”
然而,这份酒店正式员工的工作也并没有持续多久。泡沫经济破裂,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一直萎靡不振,饭店的客流不增反降,不得不开始解雇员工。原女士也不幸失去了刚刚找到的工作。在那之后,她开始频繁地更换各种非正式工作,例如为自动贩卖机补货的辅助业务、用计数器统计车站内乘客的计数工作、为大型古书店仓库理货等,这些工作的时薪都只有1 000日元上下。
原女士感叹:“已经过了50岁,但感觉未来的生活并不会有什么好转,没有像样的技能,也没有什么目标。感觉人生陷入了僵局。”
经过多次跳槽,不仅生活没有好转,收入还一再下降,她感觉自己像是被卷入了一个旋涡,一步步被拉进深渊。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生活还得继续,但应该依靠什么去前进,怎样去度过,我都不知道。或许一直这样下去,年纪越大,生活也会越来越萎靡。但我对怎么改变这个现状毫无头绪。”原女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父亲的看护——压在她身上的重担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虽然从事的都是非正式工作,但至少可以尽量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更长时间,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稳定。但其实有一个阻碍原女士长期工作的因素,那就是她在北海道农村生活的父亲。
这一切开始于三年前,一直身体健康的母亲突然去世。92岁的父亲独自留在了故乡。原女士之前从未与这个固执寡言的父亲认真交流过,但因为母亲还在,她认为母亲可以支撑着父亲。但事与愿违,母亲走在了父亲前面。
虽然周围有亲戚在,但原女士绝对无法将父亲的照顾完全交给外人。周围的人都认为,原女士仍是单身,肯定无所牵挂,这让她感受到了一种不得不由自己来照顾父亲的氛围。
“仿佛所有人都在对我说:(在所有亲人中)只有你一个人是单身,所以你可以照顾他吧,就像要把所有事情都推给我,让我一个人肩负起在身心上都很吃力的看护任务。就连我独自留在城市这件事,或许也会有很多人因此认为我自由散漫,任性地不回家吧。”
也是因为来自周遭的压力,原女士现在定期回家看望父亲。大概三个月一次,每次在家待上七到十天左右,在此期间她会帮父亲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尽可能地支持父亲的生活。但非正式工作很难允许她为了看护休假这么长时间。所以她也只能找那种两三个月短期合同的工作,四处辗转生活。但很遗憾的是,能找到的工作,条件都相当苛刻。
“最近,我在面试的公司也被问到过‘能在这里上班一年左右吗?’。我说,我得照顾老人,每两个月要休息一周,要不然会很难办。未曾想这句话出来气氛一下变得很尴尬。我觉得一般来说很难找到符合这种要求的工作。如果是作为正式员工被长期雇佣,或许还能考虑,但鉴于我现在的情况,大概不会有人愿意聘用我吧。”
原女士担心,一旦某段工作不是很顺利,就会陷入没有收入的困境,因此虽然还有年轻时积攒的存款,她却没有轻易动用,以备不时之需。当然,之所以处于如此窘境仍坚持看护父亲,其中也有着作为女儿的情感。
“也算出于一种责任感吧。总不能置父亲于不顾,对吧?但是,我也做不到坚定地说自己一定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在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同时,由于对父亲的护理负担加重,原女士对未来感到越来越迷茫。既不能抛弃需要护理的年迈父亲,也陷入了如果为照顾父亲辞职,自己就不得不成为“消失的劳动者”的窘境。
原女士表示:“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呢?就像没有带着地图的旅者一样。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人生的困境,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活下去……”
现在,她每隔两个月会帮父亲进行购物、清洁、整理家务等工作,然后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就由父亲自己一个人勉强生活。尽管处于勉强支撑的状态,她还是尽量想办法兼顾看护与工作。但是,如果未来父亲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要随时照顾该怎么办呢?原女士对此也没有答案。
(本文经授权选摘自《消失的劳动者》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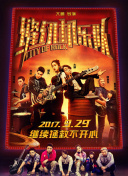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


 47847
47847 26
26


 48158
48158 46
46


 18095
18095 59
59


 76276
76276 17
17


 65573
65573 36
36


 4
4


 86478
86478 85
85


 30367
30367 78
78


 63524
63524 2
2


 62738
62738 4
4


 31856
31856 47
47


 71272
71272 50
50


 83067
83067 20
20


 99712
99712 97
97


 54978
54978 31
31


 63720
63720 90
90


 53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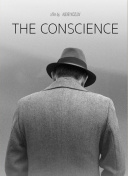

 29063
29063 54
54


 68942
68942 21
21


 89181
89181 94
94


 23218
23218 58
58


 28745
28745 52
52

 81201
81201 44
44


 17391
17391 69
69

 29549
29549 6
6


 17480
17480 70
70


 89028
89028 4
4

 98746
98746 88
88


 79267
79267 68
68


 83517
83517 81
81


 27017
27017 78
78


 54410
54410 77
77


 62398
62398 1
1


 63428
63428 58
58


 63473
63473 31
31

 47199
47199 19
19


 84052
84052 15
15


 46245
46245 22
22


 19684
19684 80
80


 22271
22271 49
49


 94874
94874


 36152
36152 35
35


 45060
45060 29
29


 74946
74946 99
99


 90160
90160 42
42

 41857
41857 2
2


 66369
66369 8
8


 47534
47534 52
52


 61701
61701 41
41


 52980
52980 33
33


 50061
50061 60
60


 68054
68054 69
69


 93840
93840 53
53


 92885
92885 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