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豆传媒色午麻豆:烂货下面都松了H-休学四年,一对母女的成长与和解
记者 / 石爱华
编辑 / 宋建华

陈阳体验做收纳师期间,在一户人家整理被孩子物品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的屋子
" 初三开学的摸底考,我女儿数学交了白卷。" 如今,陈阳再说起这件事,语气里掺杂着调侃的味道,但四年前接到老师电话的那个瞬间,她坦言 " 真的很崩溃 "。
" 交白卷 " 的第二天,女儿思思被确诊为中度的焦虑和抑郁,她提出了休学的想法。这也正好契合了陈阳当时的心理需求,"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女儿频繁请假,我也有点承受不住了 "。当时,陈阳只是觉得 " 孩子歇一歇就好了 "。
接下来,这对母女经历了一年 " 与彼此情绪过招 " 的日子。女儿休学后躲进卧室昼夜颠倒、吃外卖、上网、拒绝见人;母亲辞去国企工作,在屋外想尽办法," 百爪挠心 "。
这是一个关于休学女孩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位母亲重新审视亲子关系的心路历程。思思在成长过程中,总习惯性地顺从父母的要求,而陈阳则会把自己的期待视作对女儿最好的选择,这种需求和给予的错位曾让双方既痛苦又委屈。" 当她无法满足我对一个孩子的期待后,我才开始审视这种期待背后的焦虑和控制 "。
四年半过去,参加摸底考的那批初中生已步入大学,19 岁的思思依旧没有回归学校。但不同的是,陈阳和思思紧绷的心已经逐渐松弛下来。当母亲逐渐把重心回归到自我,女儿也开始认真思考 " 我到底想要怎样的人生 "。

和父母回老家的路上,思思拍下了沿路向日葵的美景
" 他们好像只担心休学后我无法回到学校,而不是我已经撑不住了。"
很多人问过思思,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决定休学。" 我很难说清因为哪件具体事,只是觉得身体真的撑不住了 "。
2020 年,14 岁的思思在北京朝阳区一所学校读初二,在母亲陈阳的评价里,女儿成绩不错,常在班级前 10 名。人缘也不差,善于倾听,和同学从来没有过矛盾。但从初二下学期开始,思思经常犯困、头疼,频繁请假。
" 我那时候体能差,害怕跑操 ",每天例行的 2 公里跑,是思思 " 最痛苦的时刻 "。她曾怀疑自己心脏有问题,还特意到医院体检,得知指标一切正常,她大哭了一场——因为没有理由不跑了。
" 相比跑操本身,我更害怕拖班级后腿,跑不下来会扣班里的分 ",课间操前的那节课,思思会不停看表,越快到下课时间,心里就越紧张,甚至到呕吐或者拉肚子的程度。有一回跑操,她实在难受,就跑出队伍到操场边上,结果直接吐在了校长面前。
" 孩子你怎么了 ",面对校长的关心,思思第一反应居然是恳求校长 " 不要给我们班扣分 "。
那时候,不管是学校的规定,班里的要求还是父母的期待,思思都习惯性地顺应、听话,如果自己做不到,还会愧疚。例如,每次身体难受,她都很害怕请假,怕给老师和家长添麻烦," 父母和家长都劝我再坚持一下,我怕他们认为我在偷懒 "。
初二暑假,她曾吃中药调理过一段时间,但情况没有明显好转,在初三开学的摸底考试中,思思直接昏睡过去,结果是,陈阳接到老师电话,说思思数学考试交了白卷。
对于思思的 " 睡不醒 " 和 " 头疼 ",陈阳以前没往心里去," 我当时很不理解,甚至不相信 "。陈阳从小在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育是,凡事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后面,要先考虑周围的别人和事情。" 我上学时,一天假也没请过 "。陈阳这样说自己。
陈阳和丈夫都是从小城市来到北京读书的大学生。在她的经验里," 你要想完成升学或者达成一个生活目标,势必要付出一些代价,头疼哪有学习重要 "。陈阳现在有些后悔,在思思说起自己身体不适时,她从来没说过任何心疼女儿的话," 我真的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
交白卷的第二天,思思在一家医院的精神科确诊了 " 中度焦虑 " 和 " 中度抑郁 "。事后思思和父母商量想要休息,父母带她去咨询了专业医生。医生的建议是,最好先不要休学,因为从她经手的病例看,休学孩子重回校园的例子太少了。" 说得好像,一旦休学,我的人生就要完蛋了一样 ",思思说。
父母也建议她再考虑一下,思思的感受是," 他们好像只担心我无法回到学校,而不是我已经撑不住了 "。
那天晚上,思思和父母一起开了家庭会议讨论休学问题。父亲表现得一如既往的理智,说可以尊重她的决定,但需要她自己想清楚一个问题," 休学后,你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如何完成之后的学业和生活?"
思思觉得,父亲看似开明的决定背后,实际上是把休学的问题和责任抛给了当年只有 14 岁的自己," 因为家长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
" 当时我才 14 岁,我怎么可能知道要什么生活,我只是编了一些他想听的话,说服他同意休学罢了 "。陈阳还记得,女儿的休学计划是她帮忙一起写的,对于休学后的日程,大概涵盖了学习、运动、爱好、社交等。如今回看,她觉得那份计划,是她作为家长的期待,而根本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份计划确实成了 " 一纸空文 "。

在思思闭门不出的那段日子,猫咪 " 可然 " 会到她的房间睡觉或者 " 跑酷 "
" 在情绪层面上解决问题最容易踩坑,但那个阶段,我和孩子一直在情绪上过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休学的第一年,是最煎熬的。
思思有一个比她小四岁的妹妹,原本两人同住一个房间,休学后,她不想见人,觉得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于是搬进了家里最小的一个屋子。房间里有一扇朝西的小拱窗,只有到下午才有阳光,与客厅也只隔着一个玻璃推拉门,她通常关上门,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
抑郁和焦虑带来的躯体化表现是她经常头疼、失眠," 无法做任何事情 "。思思记得,有一次头疼到直接晕了过去。而那些无法入睡的晚上,她会看一些游戏实况直播,或者刷一些没有营养的视频,直到白天太困,困到极限,才能睡着。
思思休学后,陈阳下了很大决心,辞掉了国企工作。" 外部原因是女儿休学,内部原因是我当时的工作也不开心 "。
陈阳所在的单位,作息规律,待遇不错,几乎不会有人辞职,"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劲儿。" 回看起来,陈阳认为当时的自我价值感来自外界的评价比较多,所以她会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身边人几年没有考下来的证,她一年就考完了;单位组织的羽毛球、游泳比赛,她都会认真准备,拿到第一名后,心里其实一点也不开心。" 我做什么好像都是为了得到外界认可,而不是我自己内心想要的 "。
陈阳自认为和丈夫从不 " 卷娃 ",但她不确定,她对自我长期养成的那种习惯性严格要求,会不会间接给孩子们带来无形的压力。
辞职之后,她全心投入到对思思的照顾中,开始研究做饭。理工科出身的她,还会用表格做好每日菜谱,既考虑营养搭配,还照顾思思的口味和喜好。
当她准备好一桌子饭,敲响思思房门,女儿的一句 " 不想吃 " 就能让陈阳瞬间泄气,如果思思再接一句 " 想吃外卖 ",她心底就会冒出愤怒、委屈的感觉。
" 我对那时候的自己没有什么要求,甚至连时间概念也不是很清楚 ",思思回忆说,她当时的状态就是见到人就会烦躁,那时候妈妈每天做饭,爸爸也常提议一家人出去吃饭,但她对食物提不起任何兴趣," 我点外卖,属于情绪性进食,我要靠食物去安抚自己,吃不到会很难受 "。
面对思思的反应,陈阳最初选择的方法是 " 退让 ",希望最大程度上照顾女儿的情绪," 允许她吃外卖,允许她 24 小时用手机、允许她不看书,允许她不交朋友,允许她不出门,允许她昼夜颠倒 ",陈阳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当时的允许并非真正的接纳,而是 " 忍 "。
忍耐到达一定程度,情绪会加速反噬陈阳,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方法,还会生出 " 我是不是太纵容孩子了 " 的心理。情绪来袭时,陈阳会去敲思思的门,质问她为什么要吃外卖,甚至会反问,"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或是威胁说," 我以后再也不给你做饭了 "。
陈阳爆发时,思思也会非常崩溃,要么跟母亲吵一架,要么躲在离房门最远的角落里等母亲安静下来," 因为你总感觉家长的情绪是不稳定的,一会儿特别好,一会儿又特别急躁,他们看似允许我休学,实则很焦虑,我不希望她把精力都放在我的身上 "。有一次和母亲吵完,思思很想睡一觉,于是最大剂量地服用了安眠药,但没有人发现。
" 在情绪层面上解决问题最容易踩坑,但那个阶段,我和孩子一直在情绪上过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陈阳也会去参加一些读书会,或者是听一些针对休学家长的课程。学着观察自己的情绪," 在了解了情绪的本质后,我渐渐可以不被孩子的情绪影响了 "。
" 情绪的本质来源于自己的认知,认知又来自于我过往的经历 ",陈阳拿吃外卖这件事举例," 在我以往的标准和观念里,觉得吃外卖就等于不健康,所以我不希望孩子吃外卖,所以当孩子的行为与我的认知和期望不一致时,我就会愤怒,产生情绪,但实际上情绪是自己给自己的,与别人无关,与孩子无关 "。
关注到情绪后,当陈阳对某个人的某些行为看不顺眼时,她会停一停,问问自己:我为什么看他不顺眼?是因为我对某件事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吗?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当我意识到情绪来源于自己时,我就可以管理情绪了,同时,我会真正的允许那件事儿发生 "。
" 真正的允许不是憋了一肚子气不说,而是这件事不再能影响我的情绪 "。

2023 年 11 月在国际高中试读期间,思思有一个周末很想去看海,陈阳开车带她到最近的天津海滨
思思觉得,母亲总是在不断给她输出一个信息," 就是我必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上去,否则我就是不对的,不应该的。"
母女俩除了在情绪上彼此消耗,陈阳觉得她和女儿的拧巴,还源于一个她非常明确的目标——帮女儿回到学校," 我死死地抓住这个期待,当它实现不了时,我会非常痛苦 "。
思思在房间里昼夜颠倒时,陈阳在房间外马不停蹄地为 " 女儿回到学校 " 想办法," 那时候我非常有信心,觉得可能让她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 "。
陈阳在网上找了很多教育机构和平台,还有一些夏令营,希望思思走出去。2021 年,思思在家休整一年后,陈阳经一位休学家长的介绍,了解到一出学社这个教育机构,来到这里的孩子都和思思一样,处于休学阶段。
思思决定去一出学社的原因也很简单," 我只是觉得不能一直在家待着 "。寄宿制的学社,让思思重新开始社交,回忆起那个阶段,思思觉得自己得到最大的支持是环境,在那个场域里,她觉得自己不再孤单," 并非没有朋友和玩伴的那种孤单,而是说,我发现很多孩子都和我一样,没在上学 "。
休学以后,思思屏蔽了所有同学的朋友圈,走在街上,看到穿校服的孩子,她心里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去想," 我的人生进程,是不是已经被同龄孩子落下了很多,我的世界是不是完蛋了 ",这会让思思有一点自卑,但在学社里看到很多同样处境的孩子时,这种被世界遗忘的焦虑感降低了。
2022 年秋天,在一出学社快满一学年的时候,陈阳觉得女儿距离回归学校可能已经不远了,而思思心里其实是紧张的,因为不论是学社的老师还是家长,都会问 " 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
思思觉得,母亲总是在不断给她输出一个信息," 就是我必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上去,否则我就是不对的,不应该的 "。
" 出路就是那些,都摆在眼前,回到原来的学校、读国际学校、出国 ",陈阳说,思思从一出学社离开后,她和丈夫又跟女儿一起讨论了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她认为自己把选择权交给了女儿,陈阳说," 孩子爸爸帮忙分析了每种选择的利弊供思思参考,但我觉得他心里有自己的答案,于是他在阐述观点时会着重说那个他认为好的 "。在听完父亲的分析后,思思决定回到原来的学校继续读书。
再次回到初二课堂,已经过去两年多,思思在新的班级里,心里多少会有点窘迫," 毕竟我比那些孩子大三岁 "。
思思坦言,当时选择回到学校,在心理上是 " 勉强的 "," 因为我不敢说我想继续待在家里,我怕他们接受不了 "。另一边,看到女儿重回学校的陈阳非常高兴," 如果不用欣喜若狂来形容,那也是如释重负 "。
可好景不长,思思又开始出现了疲惫、困倦的症状。"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梦,感到非常累 "。思思又开始频繁请假,事情好像又回到了起点,陈阳的心情也随着思思的状态起起伏伏," 因为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她回到学校的这个目标上,所有的事情都围绕这件事波动 ",陈阳说。
复学三个月后,思思再次休学回家。
陈阳没有放弃努力,很快她又找了一家国际学校," 我觉得我已经为她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2024 年,思思来到国际学校," 这是一家很好、很自由的学校 ",思思看到了一些与以前学校不同的场景," 大家在回答问题时,真的会站起来长篇大论自己的观点,去探讨一个问题,这是我以往在学校里没有接触过的 "。
自由的学习氛围也抵不过身体上的不适。思思当时停止使用了抗抑郁药物,但症状其实一直没有好。在国际学校念书时,她经常在宿舍里困到无法起床,但又不敢跟老师请假," 我怕他们误以为我偷懒 "。
" 我那时候经常会有无法呼吸的感觉,明明有氧气,感觉吸不到肺里 ",有一次在课上,思思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像有人掐住了喉咙,她没来得及跟老师打招呼,就飞奔到教室外面,缓了半节课才正常。" 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
那段时间,老师向陈阳反馈,思思经常在宿舍睡觉,不去上课,吃饭也经常用方便面和快餐凑合。陈阳记得,是丈夫先发现女儿状态不对,丈夫推测," 孩子应该不想继续在那里上学了 "。
他们想,与其如此,还不如让思思回家," 至少能好好吃饭 "。在国际学校大概半年后,思思再次退学,但此时的思思,已经不再把自己关在房间,而是搬回去与妹妹同住了。
" 我已经使了浑身解数,但孩子还是没有按照我期待的方向走 ",这四年的现实,给陈阳最大的教育就是," 要放下对孩子的期待 ",当思思无法满足她作为母亲的期待时,她开始审视,她对思思期待背后的 " 焦虑、恐惧与控制 "。陈阳也渐渐意识到," 我要先把自己的生活整明白,而不是一直盯着孩子 "。

从孩子休学的焦虑中走出来后,陈阳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图为陈阳在上舞蹈课
" 学历、工资、工作,都不能定义什么是好的生命状态。"
" 我放下了让她重返校园的期待,或者说我到现在才真正接纳了她休学这件事 ",思思几次重返校园无果而终后,陈阳逐渐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去做兼职收纳师、去做义工,去上课,去参加合唱团,发展自己的爱好。" 难道孩子休学了,我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吗?"
反观自己成长的过程,陈阳一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从小到大就按部就班地按照父母的要求去考学、工作。这一观念,被她复制到自己的家庭中。所以在她看来,以前的思思似乎缺少了一些学习的 " 志向 " 和 " 内驱力 ",是一个接一个阶段性的外部指标,推动着孩子去被动学习," 她甚至被我和爸爸训练得习惯性顺从了 "。
" 要改变这种现状,我必须先把自己整明白 "。陈阳心态的改变,体现在很多小事上,她会告诉孩子,衣服是身体的外延,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就是整理好自己的状态。垃圾就像是烦恼,丢掉垃圾,就是清除自己的烦恼。她不再要求孩子去做家务,而是告诉孩子,做家务是为了什么。
在自己的感受不好时,陈阳不再去迎合外界,比如她兼职做义工,有一件紧急的事情找到她帮忙,换做以前,她即使手头有事,也会考虑对方感受,答应下来。现在她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现在没有精力,不能马上着手去做,如果您着急,请您问问别人吧 "。
陈阳和思思的关系也有所缓和,有时候一家人会坐在一起复盘这四年的经历,思思偶尔还会突然在聊天时说出一个梗,逗乐全家人,她现在可以用幽默地语气去回忆那段初中跑操的经历," 有一次跑步,我吐在了前面同学的裤子上,是红色的,同学以为是血,实际上是我上节课偷吃了牛肉干 "。
对于未来和出路,思思还是有些迷茫,很多 " 过来人 " 都跟她说过," 人总会走出一条路 ",但在思思看来,其实这也不过是 " 人人都懂的道理 ",对于此刻正处于休学之中的人来说,毫无焦虑是不可能的。
最近一段时间,思思看到母亲的变化,心里也会轻松很多。四月的一个星期五,陈阳出门参加了一个合唱团,思思还表达了也想参加的想法," 如果我去了,肯定是年纪最小的,那大家肯定很稀罕我 "。陈阳发现,自己好好生活后,孩子可能潜移默化地会得到正向的影响。
" 以前,我总以为给他们好的物质条件就是好的 ",陈阳在做兼职收纳师之后,曾见过很多有娃的家庭,他们的客厅被孩子的玩具占领,或者一个刚刚 10 个月大,不会走路的孩子,已经有了很多双鞋。在陈阳的家里,也有着很多这样的玩具和衣物," 但这真的是孩子所需要的吗?
陈阳觉得,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上,以往过多注重学习和知识的教育,如果可以重来,她想先教会孩子去 " 深度的生活 ",从认真地管理好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开始。
陈阳以前觉得,考大学是一条必经之路," 有什么想法先考了再说 ",但她最近改变了这种想法," 我经常去想,我理想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这好像不是用学历、收入、工种去衡量的 ",与其让孩子 " 必须考大学 " 不如去拥有一个热爱生活的生命状态," 将来做什么工作都可以 "。
去年,思思以社会身份参加了高中会考。她目前能想到的路径,还是等完成会考科目后,以社会身份去参加高考。
" 我其实很喜欢学习,我在尝试找回学习的状态,但现实情况是,我的精力还是很难集中 ",但思思开始尝试在每一件小事中去肯定自己,比如背了一个单词;或者电脑不够高,她置办了一个支架,也很有成就感;又比如早晨打开窗户,外面的空气很新鲜,她也很高兴。" 哪怕我只是坐得比刚才直了一点,我也会夸赞自己很棒 "。
四年间,很多人问过思思为何休学,思思认为与其询问休学的孩子,不如去问问那些尚在学校里的孩子为什么上学,她认为所有孩子应该都清楚自己为何上学,否则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好像很少有家长去问孩子这个问题吧?"。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陈阳、思思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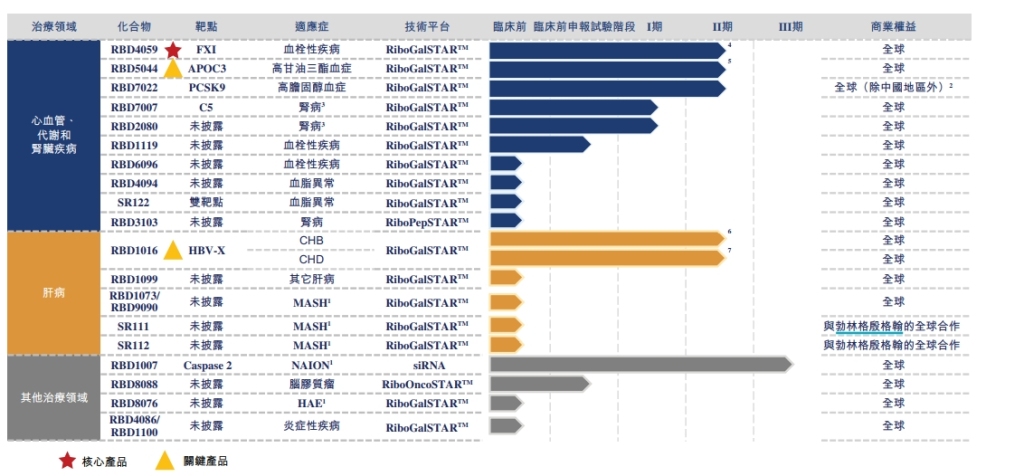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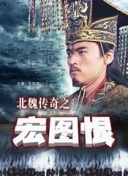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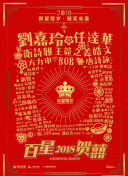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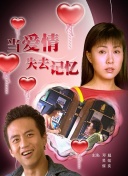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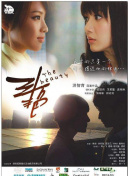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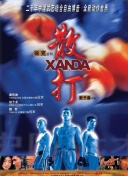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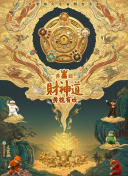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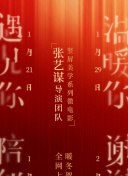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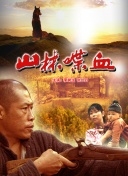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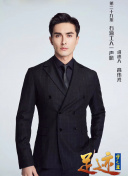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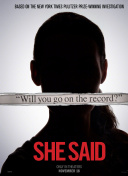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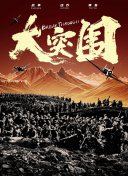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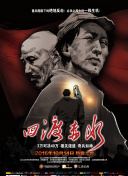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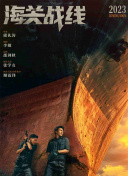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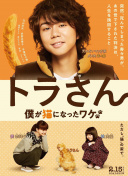
 47847
47847 26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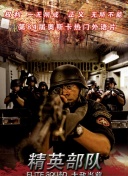 48158
48158 46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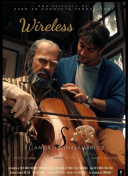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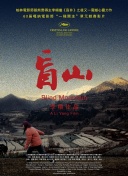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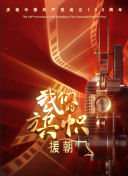 18095
18095 59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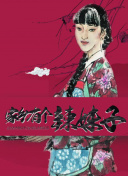 76276
7627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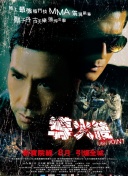 17
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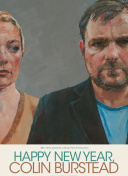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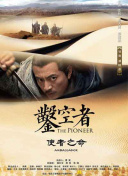 65573
65573 36
36


 63128
631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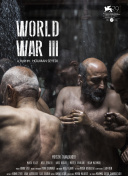 4
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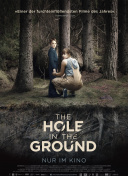


 86478
86478 85
8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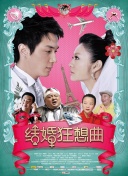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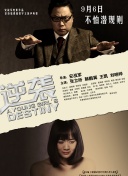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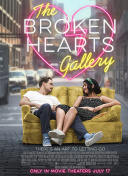
 30367
30367 78
7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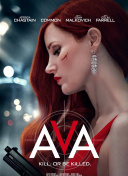


 63524
6352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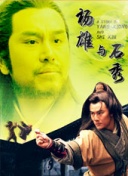 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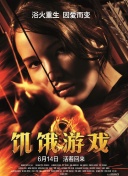
 62738
62738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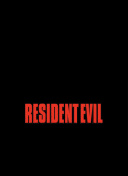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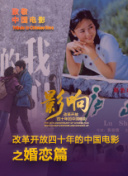 31856
31856 47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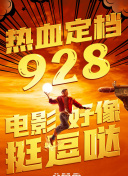

 71272
71272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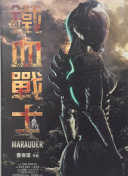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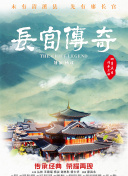
 83067
83067 20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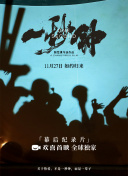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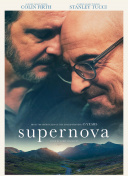
 99712
99712 97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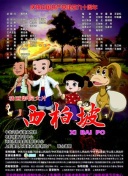 54978
5497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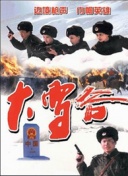 31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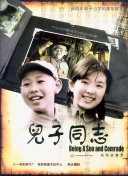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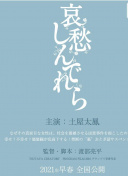 63720
63720 90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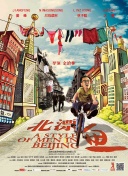
 94331
94331 53
5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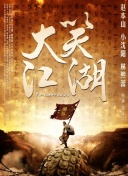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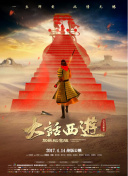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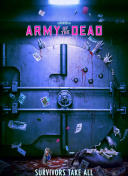
 29063
29063 54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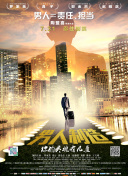

 68942
6894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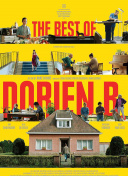 21
2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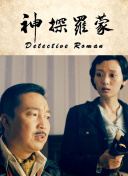


 89181
89181 94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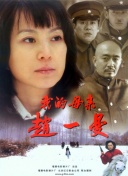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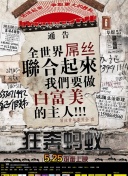
 23218
23218 58
58


 28745
28745 52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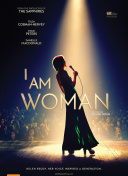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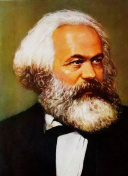 81201
81201 44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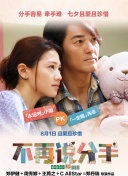

 17391
17391 69
69


 29549
29549 6
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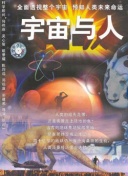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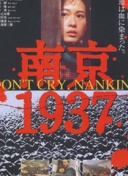

 17480
17480 70
7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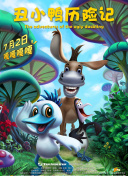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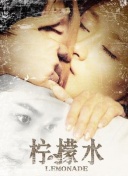
 89028
89028 4
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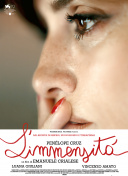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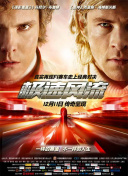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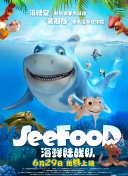 98746
98746 88
88


 79267
79267 68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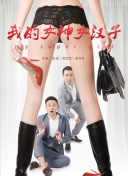

 83517
835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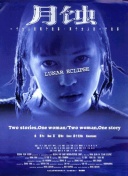 81
81

 27017
2701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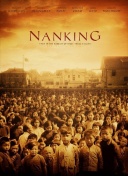 78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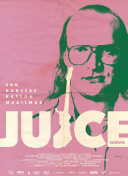 77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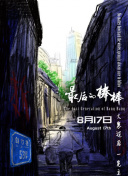
 62398
6239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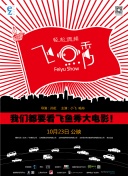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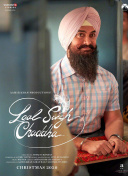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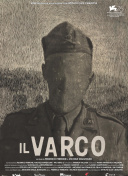
 63428
6342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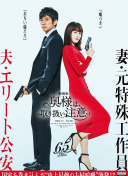 58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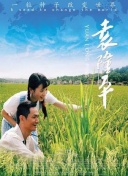 63473
63473 31
3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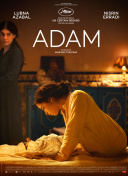


 47199
47199 19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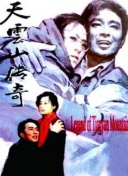

 84052
84052 15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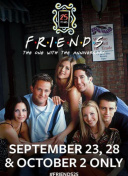

 46245
4624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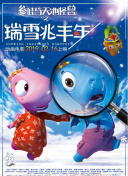 22
22


 19684
19684 80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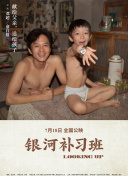 22271
22271 49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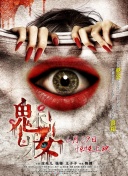 94874
94874 50
5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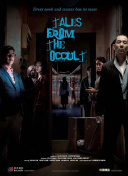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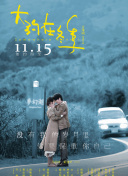
 36152
36152 35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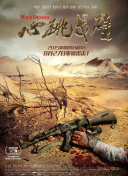

 45060
45060 29
2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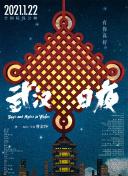


 74946
7494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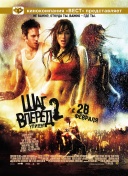 99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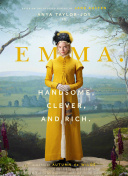 90160
90160 42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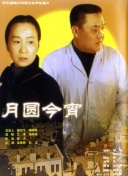

 41857
41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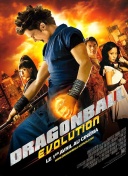
 66369
66369 8
8


 47534
4753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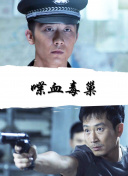


 61701
61701 41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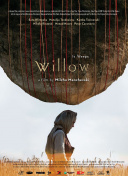

 52980
52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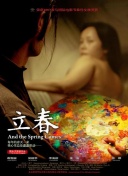 50061
50061 60
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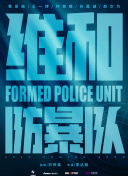


 68054
68054 69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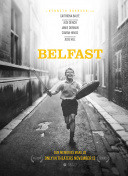 93840
93840 53
5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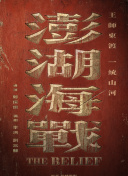


 92885
92885 11
11